100多年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世界岛或心脏地带理论。在该理论中,相连的欧洲、亚洲、非洲组成世界岛,周围则是美洲、澳洲、日本列岛、英伦列岛等较小的岛屿。而世界岛又可分为六个区域,由西欧与中欧组成的欧洲沿岸地带、由印度、中国、东南亚、韩国和东西伯利亚组成的季风亚洲或沿岸地带、阿拉伯半岛、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心脏地带。
他认为,欧洲、亚洲由于人口众多、面积庞大, 它是世界上政治、经济力量的中心, 而且还是文化、宗教和价值的诞生地,因此,欧亚大陆属于世界岛上的枢纽地带。

他同时还认为,上图中的心脏地带是一片位于欧亚大陆中央与北方的大平原,范围是从伏尔加河到长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这个区域的北方海岸结冰又平直,区内的大河包括的勒拿河、鄂毕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叶尼塞河都不入南方海洋,因此海洋势力就无法深入,而心脏地带还有一个大型的低地平原,形成一条从西伯利亚通往欧洲的大道,很适合有高交通运动能力的陆地强权。
从麦金德的这段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匈奴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在心脏地带崛起为陆地帝国,然后向西通过今天的乌克兰、波兰等地向中西欧地区发动冲击,让位于西欧平原与东欧平原之间的中欧平原烽火连天,很多国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亡国又不断重建,我们最熟知的当然就是波兰,向东、向南就是向中东地区和东亚大陆发动冲击,伊尔汗国和元朝都是这种冲击的结果。今天普京对乌克兰的征服行动,不过是历史的延续。

如此也就有了麦金德那三句著名的论断:
-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带”;
-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
在15世纪末期开启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属于陆权时代,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国的陆续崛起,世界就进入了陆权与海权相争的时代。麦金德特别警告说,心脏地带国家建立起陆权之后就会向世界岛的边缘地带扩张,特别是与德国的结盟会扭转海权与陆权国家的力量对比。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一旦边缘地带强国征服了心脏地带,这就是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时期法、德对沙俄的征服行动,也一样会扭转海权与陆权的力量对比。
当心脏地带国家征服了边缘地带强国之后,或者边缘地带强国征服了心脏地带之后,就会建立起在陆地上不受挑战的大陆强权,当大陆强权又拥有足够资源建造舰队时,便足以击败海洋强权。而“心脏地带”理论同时指出,没有这两项条件,海洋强权便能胜过陆地强权。因此,如果海洋强权要压抑大陆强权的崛起,便需要从“世界岛”的两端海岸遏制大陆强权的出海口。
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何在拿破仑战争中作为海洋强权的大英帝国为什么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沙俄,在一战二战中又不遗余力地支持沙俄和苏联,在冷战中又全力扶持德法和东方大国,他们的目的都是一个,防止形成一个在陆地上完全不受挑战的大陆强权国家或集团,这样的大陆强权一旦形成,就会颠覆海洋强权。
二战结束之前的1943年,麦金德就会已经预判到苏联作为战胜国会成为心脏地带强国,为了防止苏联进一步征服欧洲与亚洲边缘地带,进一步成为在陆地上完全不受挑战的大陆强权,他就提出了米德兰海的概念。
他认为恢复世界秩序首先应关注的就是密苏里河和叶尼塞河之间的地区,这里是商业航行主干线的支点,也是阿基米德试图要找到的撬动整个世界的支点。密苏里河是美洲的河流,横框美国中部,而叶尼塞河是属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河流。
他因此得出结论:“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成为德国的征服者,它必将会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陆权国家”。事实是,战后的苏联控制了四分之一个德国,那就是东德。然后,麦金德就提出了战后最重要的地理概念,——“米德兰海”(Midland Ocean), 即北大西洋和它的附属海域与河流流域,附属海域包括地中海、波罗的海、北冰洋和加勒比海,河流流域则涵盖北美和欧洲的河流。麦金德说:“‘米德兰海’有三个核心要素——法国桥头堡,环以天堑的英国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力和经济基础”,参考下面的地图。这一地理概念实际上是麦金德为西方海权力量应对“心脏地带”陆权力量而设想的一个跨大西洋军事集团组织,这就是6年后出现的北约。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华约和苏联的解体,作为心脏地带强国的俄罗斯丧失了包括东德在内的广大东欧地区和苏联原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权,说明麦金德依托米德兰海概念设计的地理战略获得了胜利。
历史就是现实。
冷战时期,北约的前沿在德国,法国是北约桥头堡。苏联解体之后,北约的前沿已经抵达波罗的海三国,随着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北约前沿开始向黑海西岸进发,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甚至芬兰就成为北约或欧洲的桥头堡。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美国撤出欧洲已经是事实,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只是一个军火商的角色,欧洲出钱购买美国军火然后支援乌克兰,这意味着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感正在迅速下降。
2025年7月17日,德国总理访问英国,双方正式签署《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友好与双边合作条约》,该条约涵盖安全、防务、气候、科技等多领域,这意味着英德军事同盟关系已经确立。此前,英法也签署了类似的同盟条约。考虑到德法在欧盟中同处于核心地位,英德、英法条约的确立,意味着英、法、德军事同盟已经形成,它们的对手当然是俄罗斯,这意味着黑海周边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一线的战争,正在成为欧洲战争。
当英法德军事同盟成立之后,放眼四顾,他们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是能源安全。
当黑海周边甚至波罗的海西岸战争打响之后,意味着欧洲再也不能倚重俄罗斯的能源,俄罗斯等东方国家的盟友就包括伊朗,随着美国无力维护中东和平,伊朗与以色列和阿拉伯逊尼派国家之间的争端将长期化,这意味着中东也不是欧洲可以倚重的能源供给基地。
欧洲需要建立自己的能源“大后方”。
第二是装备大后方。
俄乌战争打响之后,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遭遇了装备短缺的严重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二战之后的欧洲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和平时期对装备的需求与战争时期截然不同,比如一辆卡车在和平时期的寿命可以长达十几年甚至更长,但战争时期却只有几天或几个月,坦克大炮更是如此,炮弹等军火物资在战争时期的需求会像火山一样剧烈喷发,欧洲在和平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就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再加上战争持续之后本国的工业体系有可能遭遇对方的破坏,此时,就需要建立装备供给的“大后方”。
美国人正日趋孤立,而且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开始单边行事,再加上一旦失去加拿大的原油、天然气和铀进口,美国并不具备太大的能源出口能力。
此时,可以满足欧洲能源大后方、装备大后方需求的国家还有谁?或只有一个政治稳定、遵守契约精神的加拿大,这两点都十分重要,在战时时期,只有政治稳定并遵守契约精神的国家才能成为自己的能源与装备大后方。也只有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铀、有色金属、农产品和装备生产能力才能满足欧洲的战时需求。
在这个大争时代,加拿大是欧洲稳定的大后方。
然后我们再看看北太平洋地区。

“米德兰海”的概念可以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北太平洋地区,韩国是桥头堡,日本、湾湾、菲律宾承担的是亚洲“英国”的角色,是一道天堑,美国、加拿大是物资供给基地。
对抗时代已经到来,中日韩等国会面临英法德一样的问题:
第一是能源安全,中东乱局,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南海争夺,随时都可能掐断中东、非洲至亚洲的能源与原材料运输线,各国怎么设计自己的能源安全?
第二,今天发生在欧洲的俄乌战争属于小体量的战争,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制造能力都有限,即便俄罗斯想发动全面战争,很可能还要受制于装备生产能力。但亚洲不同,以亚洲各国的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一旦爆发战争就是真正的大战。到那时,谁会成为自己进行装备补充的可靠基地?
加拿大依旧是亚洲国家稳定的能源供给基地,甚至还是装备供给基地。
其实,亚洲国家觉醒的比欧洲国家更早,这从一份股东名单上可以得到结论。7月上旬,加拿大开始从西海岸向亚洲出口液化天然气(LNG),这个巨型项目的股东就包括英国壳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中国石油、韩国国家天然气公司和日本三菱财团,中国自中东和美国原油进口下降的同时,反而成为加拿大海上石油出口的第一大买家,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供应链转移就说明了一切。
与欧洲的英法德一样,加拿大显然也是亚洲很多主要国家能源和装备制造的大后方。
美国在战后建立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正在加速解体,中国正在回归自己的历史地位,日本、英国、德国、法国也正在回归自己的历史定位,伴随新的全球地缘构架的形成,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尤其是能源产业链正在开启大重构,此时,过去并不起眼的加拿大正在发现,基于能源和装备需求,大家都来了。
最近,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了这样一句话,自己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都是各国来谈合作的。对于政治人物的话本来不必当真,源于政治在很多时候等同于演戏,但如果看到全球的地缘政治正在进行剧烈的重组,与之相伴的就是全球产业链需要大重构,卡尼总理所言显然不虚。
特朗普代表美国从欧洲撤出,直接推动欧洲地缘政治的重组,也必然导致亚洲地缘政治的重组,最终就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大重构,让加拿大成为欧洲能源与装备最可靠的大后方,也成为亚洲一些国家的能源大后方;特朗普声称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直接推动了加拿大的国家觉醒,在构建起加拿大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同时让加拿大的对外政治、军事与经济政策更具独立性,所以,特朗普有可能正在开启加拿大的镀金时代。
这是一个大重构的时代,即重塑世界,也会重塑很多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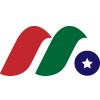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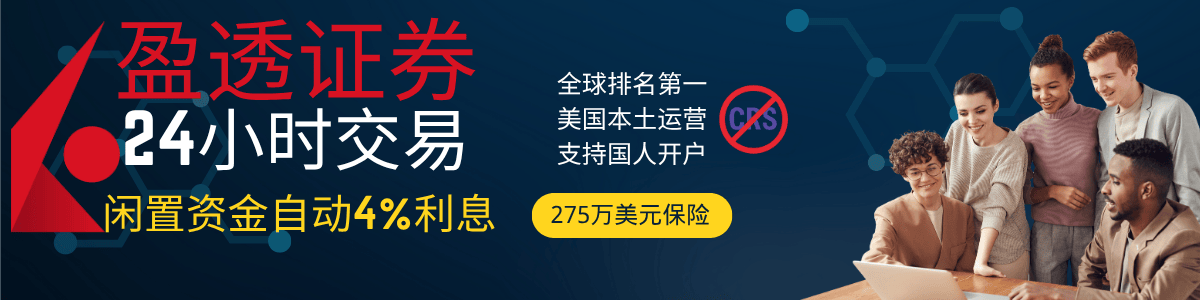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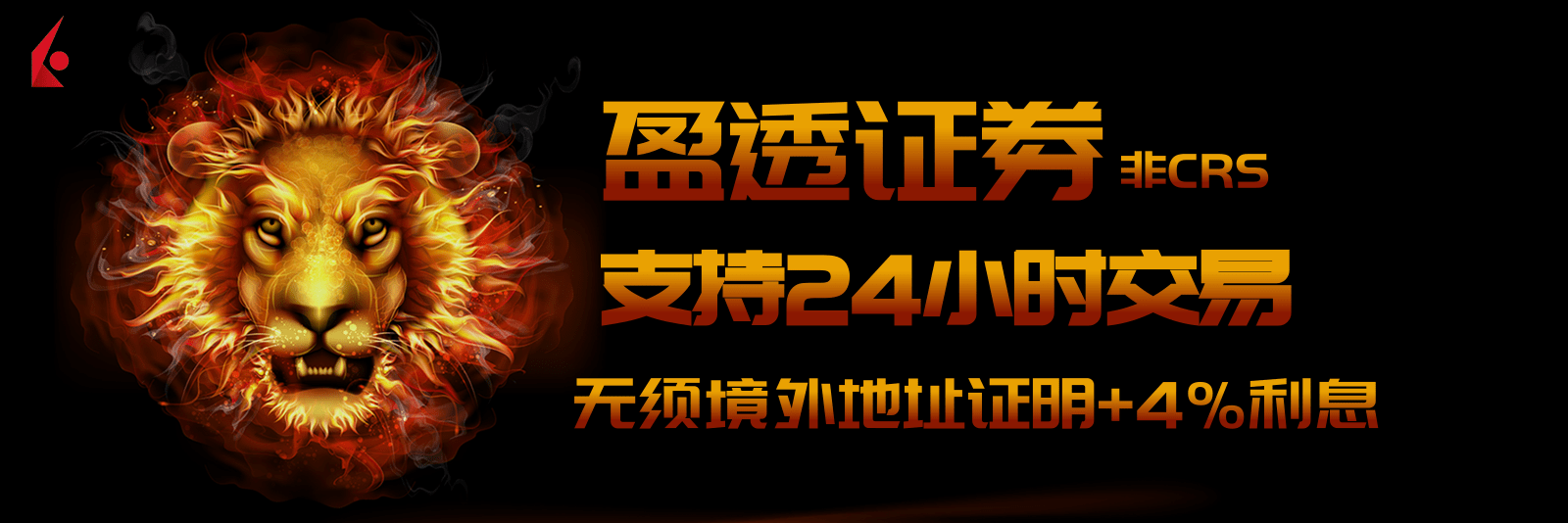












评论